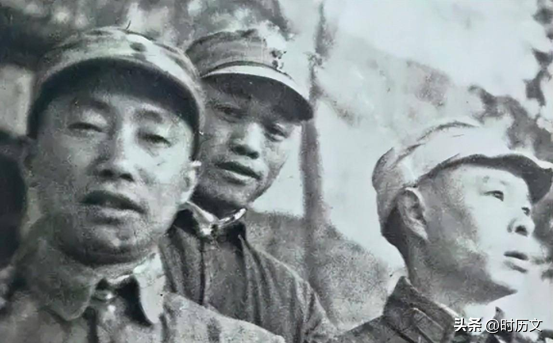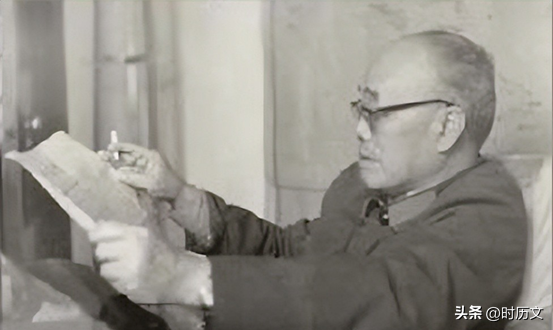刘平平平
他在大西北41年,官至大军区政委,后被取消原待遇,每月发200元
“老冼,你怎么就回到了师级待遇?”1983年初的兰州总院病房里,一名旧部压低声音问。冼恒汉摇了摇头,没有多言,右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,意思是“说来话长”。短短一句对话,把这位开国中将跌宕的后半生拉到众人眼前。
1929年,广西宾阳的青年冼恒汉踏进百色起义的队伍。那一年,他才十八岁,却已能熟练背出《布尔什维克》杂志上的口号。入红七军、远赴瑞金、被调湘赣地方武装——三年间几度改编,他兜里那本《新青年》早被磨破,仍舍不得扔。1933年组成红六军团,他跟随萧克、王震挥师乌蒙山;1935年在贵州遵义南部突围,他首次担任师政治处主任。此后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,红二方面军成形,他的军政工作从此离不开“大西南与大西北”这七个字。
长征结束,抗战爆发。冼恒汉编入八路军120师,砍树修工事、熬粥接难民,晋西北的草木风声皆可作教材,他自嘲“口袋里装着《政治工作条例》,鞋底却是黄土”。1943年冬,他在兴县前沿组织一场“火线入党”仪式,29名战士端着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宣誓,这段插曲后来被写进晋绥军区党史。
进入解放战争,彭德怀把贺龙部改编为西北野战军,第一纵队成立,冼恒汉出任纵队政治部主任。沙家店的冲锋、羊马城的夜战,他常站在通信壕里大喊:“不许乱!枪口抬高一寸!”声音嘶哑到第二天还在冒血丝。1949年初西安解放,纵队番号变为第一军,他随军一路西进。至此,冼恒汉与西北的黄沙戈壁再难分开。
新中国成立后,他在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、主任两个位置上一干就是六年。1955年授衔,41岁,红底金星的中将领章闪亮;与此同时,军区体制大调整,兰州军区独立,他升任政委,成为新中国第一批“大军区正职中将”。那时他常说:“哪怕西北只有铆钉厂,也能拧出工业化的螺丝。”
转折出现在1967年。甘肃省委主要负责人被隔离审查,中央指令军队支左。冼恒汉临危兼任省革委会主任、省委第一书记。铁路、电力、冶金、石油——几乎所有关键部门都要军代表参与,他在日记里写过一句:“政治挂帅,但生产不能丢。”遗憾的是,形势发展远超个人掌控。兰州铁路局两派对立愈演愈烈,冲突不断,被上纲上线为“路线问题”的材料也越堆越高。
1977年,他被要求“离兰州、候安排”,正式文件认定存在“严重路线错误”。调令下来,去向却空白。他从年富力强熬到鬓发夹雪,等待了足足五年。1982年初返兰“接受组织处理”时,骤然得知:原副大军区职待遇取消,按地、师级安置,月发生活费两百元。消息传来,他在院内突发大面积心梗,抢救两昼夜才脱险。
两百元在当年并非微薄,问题是他要自找住房、交暖气费,还得养活常年随侍的老伴。住处选在兰州肖家巷一栋旧砖楼,墙皮斑驳,冬天屋里温度常常零度出头。有意思的是,他仍坚持每天五点起床背《古文观止》,说是“防痴呆”。街坊见面寒暄,总能听见他大声问好,仿佛胸前还别着将星。
1983年夏,他忍痛写下十二页申诉材料。措辞直白:“本人确有执行不当之处,但决非谋私,也无意压制群众自发组织。”材料上报总政治部。次年春,总政电话打到兰州:“原处理偏重,按正军级离休。”政策一旦纠正,住房、医保、警卫员统统归位。熟识的老兵说:“老冼终于又能穿那身呢大衣去晒太阳了。”
此后十年,他极少公开谈及当年的跌宕。偶尔有人请教,他只一句:“组织决定,我服从。”1993年1月31日,冼恒汉病逝,终年八十二岁。葬礼简单,灵柩覆盖的仍是那面鲜红的军旗。人们或许还在争论功过,戈壁风沙却早已吹平当年残留的弹孔。